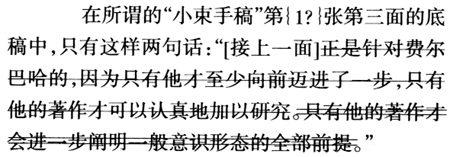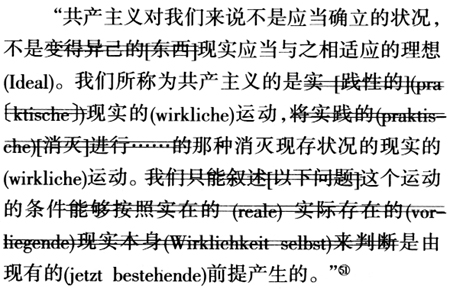【内容提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提法针对的并非是恩格斯笔下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这种做法把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抽象范畴和哲学词句。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跳出意识形态”、从哲学回到现实。因此,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是彼岸的理想、先验的圣物,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个人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生成性运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手稿第18页的右栏上,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底稿旁写下了大段的补充。其中有一段话尤为引人注目:“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一般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前一页恩格斯所写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②的回应。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认同恩格斯的表述,因此,“这一段文字与其说是底稿的一部分,还不如说像是写给恩格斯看的”③。
广松涉把这段话视为马克思思想落后于恩格斯的论据,其理由是:这段话“将恩格斯在手稿中随处所尝试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恩格斯不是作为理想和运动,而是作为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来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推翻了”④。我认为,这种解释至少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按照广松涉的理解,恩格斯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是理想,不是运动,而是应然状态。然而,马克思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是应然状态,不是理想,而是现实运动。也就是说,所谓的“共产主义”要么被理解为“理想”、“应然状态”,要么被理解为“现实运动”(前者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俘虏”即“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后者则是马克思的观点),而单单不可能如广松涉笔下的恩格斯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既不是理想,也不是运动,却还是应然状态。因为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不是理想而是应然状态”这样的表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望月清司的区分至少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他认为,相对于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运动”来理解,恩格斯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是‘运动’,而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这是一种逃避大工业、回归田园诗般的‘地域性共产主义’的做法”⑤。但这样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恩格斯的思想”却颇值得怀疑。针对“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运动”这样的说法(广松涉持相同意见),恩格斯本人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⑥;而所谓“恩格斯理解的共产主义是逃避大工业、回归田园诗的”的说法同样缺乏根据,相反,恩格斯明确表示,这种拒绝现代文明、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美好的田园社会”的空想“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⑦。望月清司进一步认为,对于恩格斯笔下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社会”,“那一字迹丑陋的作者绝不可能坐视不管,他必须在手稿阶段就使得这一节彻底茶化”⑧。
综上来看,撇开具体的问题,广松涉和望月清司在以下两点上达成了共识:首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提法针对的是恩格斯笔下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在于,前者把“共产主义”视为“运动”,后者则视为“应然状态”(广松涉)或“理想”(望月清司)。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都把马克思的这一段增补作了简单化的理解——他们都在共产主义是“运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是,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注意:马克思的着重号打在“现实的”上,而不是“运动”上)。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而言,“状态”、“理想”的对立面不是“运动”,而是“现实的”(马克思正是也仅仅是在这三个词上打了着重号),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共产主义是不是运动——因为这样仍然可能导致误解——而在于是不是“现实的”:共产主义是有别于思想运动的现实运动。因为,所谓的“解放”有“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⑨之分,真正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⑩。如果说“共产主义不是理想”是就“理想”的非现实性而言的,突出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的现实性,那么,这段话就并非直接针对恩格斯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11),而是马克思把恩格斯的论述改成故意开玩笑的戏谑之语后,从正反两面写下的他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相应地,批判的对象也不是恩格斯,而一定另有其人。
二、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及其非批判性
如前所述,促使马克思公然声明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原因,是其论敌把共产主义非现实化、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根据《形态》的标题,即“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主要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和德国社会主义。
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就是他的上帝,拥有一切完美的属性,是模型化的、典范化的、理想化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12)。在这个意义上,他“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谓词”(13),这样,共产主义就变成了爱的宗教。鲍威尔在《神圣家族》这部书中看到了“现实的人道主义”(der realeHumanismus)这个词,便得出了“《神圣家族》的作者”是费尔巴哈派的结论,认为德国共产主义是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为支柱的(14)。他幻想地认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所以取代‘唯灵论的地位’只是为了赢得崇敬。他继续幻想:那时候‘灵魂将得救,人间将成为天国,天国将成为人间。’(神学家总是念念不忘天国)”(15)。对共产主义者一无所知的施蒂纳也给马克思扣上了费尔巴哈派的帽子(16),他认为,“共产主义者想把社会变成最高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又想把自己的‘财产’作为采邑给予单独的个人”(17)。真正的社会主义则“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18),他们相信费尔巴哈的话,“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19),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20)。
总括地说,费尔巴哈“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德国社会主义把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的说辞奉为圣经,鲍威尔相信德国共产主义是以费尔巴哈为支柱的,他和施蒂纳都“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21)。也就是说,当时德国所有的批判家在这一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前两类人对这种“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持正面意见,后两位则激烈地反对它。这就容易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似乎《形态》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费尔巴哈的,因为既然《形态》中的所有论敌——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以及德国社会主义——都轻信了费尔巴哈“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尤其是鲍威尔和施蒂纳还直接指认马克思恩格斯为费尔巴哈派,那么,他们的长篇大论当然是要撇开自己与费尔巴哈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是费尔巴哈派、“实体”的信徒的无稽之谈甚至不需要再多费笔墨,这一点仅从手稿的创作过程中的一处修改就可以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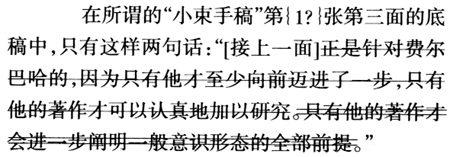
但是,前后这两句话分别先后被恩格斯在起稿时和马克思阅读时删除了。(22)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表明自己与费尔巴哈的根本不同的——“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费尔巴哈“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从而“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地方,“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23)。换言之,在反对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的奇谈怪论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和鲍威尔、施蒂纳是一致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如果《形态》主要针对的真是费尔巴哈(顺带只在澄清歪曲的意义上反对一下鲍威尔和施蒂纳),那么其第一卷只需第一章就足矣。问题是,在第一卷中,针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部分“莱比锡宗教会议”所花的文字是《费尔巴哈》章的六倍多,仅仅作一澄清是绝不可能如此费工夫的。因此,仅从文字篇幅上就可以判断,《形态》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撇开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或者澄清鲍威尔和施蒂纳把他们歪曲为费尔巴哈派的做法。从其内在的逻辑看,马克思反对施蒂纳,最重要的根本不是因为施蒂纳对他的歪曲,而是因为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换句话说,虽然马克思和施蒂纳都批判费尔巴哈,但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完全不同——施蒂纳无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前提,并与这一“理想”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生死斗争,试图把被理想化了的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在思想中加以扬弃;相反,马克思根本不承认费尔巴哈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根本反对任何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一句话,施蒂纳反对的是被理想化了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反对的是任何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
马克思认为,这种做法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泥潭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24),因为,中世纪以来的德国除了思辨能力之外在其他一切方面都落后于英法等先进国家(25),德国“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26)。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与“共产主义运动”相适应的阶段,英法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现实利益在理论上的表达——渡过莱茵河后就与“德国的哲学的历史观”(die deutsche philosoph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27)相结合并立即“德国化”为其特有的思辨形式。和康德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理解为“实践理性”的要求、把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理解为“自由意志”一样,现代德国批判家把法国共产主义理解为“真正的社会”、“实现人的本质”的要求,“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28)。就这样,法国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就被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剔除了一切经验的、现实的、唯物的因素,稀薄为纯粹的、抽象的、独立的“怪影”,阉割为空洞的词句、神圣的观念、彼岸的理想。马克思认为,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是把它重新说成是某种抽象的“类的自我产生”,变成为了赢得神圣的“崇敬”这一天国财产的神秘圣物,变成了和“批判”相同的乍看起来“震撼世界”实则无害化的词句,变成了某种在头脑中、在玄想中、在天空中游荡的“幽灵”(Gespenst)。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9)有人误以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正面观点(30)。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是这样说的——“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31)。只要联系《形态》中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马克思认为,包括鲍威尔和施蒂纳在内的“所有现代的批判的思辨哲学家都相信独立化的思想、具体化的思想、怪影(Gespenster)曾经统治过并且还继续统治着世界”(32),因此,他们相信历史就是“怪影的历史”(Gespenstergeschichte)(33)。在“莱比锡宗教会议”一节中,马克思讽刺鲍威尔说,“自我意识必须像怪影一般地游荡,直到它把导源于它而又汇集于它的万物全部吸回本身为止”(Das SelbstbewuA1Y701.jpgtsein muA1Y701.jpg solangewieeinGespenstumgehen, bisesalle Dinge, die von? ihm und zuihmsind, in sichzurückgenommenhat. )(34);在批判施蒂纳时,马克思嘲讽他说,“神圣的精神真像怪影一样在游荡着”(Der heilige Geist gehtalsGespenst um. )(35)。再对照《共产党宣言》的开头,“EinGespenst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是模仿意识形态家们“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然后用“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来表明,自己所说的共产主义与此截然不同。相反,如果说经过《形态》这一“清算哲学信仰”洗礼的马克思还会把“共产主义”从正面“隐喻为”Gespenst,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照此理解,在一切文明国家使资本家阶级感到恐慌并试图联合起来对之进行绞杀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成了游荡的“影子”(36),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就变成了思想领域里的斗争、词句的斗争、考尔巴赫描绘过的神圣的“匈奴人之战”。这样一来,所谓的“共产主义”跟意识形态家们的概念、精神、理想、圣物便毫无二致,只是找了一个不同于“人的本质”、“自我意识”、“唯一者”的“社会”作为最高理想,用这个理想在观念里反对其他“错误”的、不那么完满的理想,只要“共产主义者”把旧的观念从自己的头脑中挤出去,不但旧观念被剿灭了,旧世界也一起被真正地消灭了。因此,“共产主义”对旧世界的批判就变成了思想斗争和言语暴力。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批判哪怕在思想中把旧世界扬弃一百次,对于现实世界的触动仍然等于零,哪怕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无数遍,对于实际发展也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批判只是取消了批判家对这些观念的私人看法,不仅现存世界没有发生半点变化,甚至在别人的头脑中,这些观念依然存在,并且将一直存在下去。因为,只要没有离开思辨的基地,只要仍然在观念的领域里转圈,“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下掩盖着的只能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37),“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38)!随着“人的本质”、“自我意识”、“唯一者”或者还有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鱼贯而过,所有非人的现实都变成了主体的自我确证、作为环节得到了保留;除了哲学词句之外,现存世界的现状原封不动。
这是因为,观念上的对立乃是现实对立在头脑中的反映,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斗争、人的本质和唯一者的斗争乃是现存世界中自然界和人的斗争在哲学词句上的再现,“‘两极的对立’的观念是以对人和自然界的斗争的观察为基础的”(39)。实体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自我意识则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40)。或者说,哲学家们将其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是“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41),而“自我意识”和“唯一者”则是在重压下艰难生存并试图反抗这种压迫的现实的个人。因此,哲学对立仅仅在哲学的范围内是永远不可能得到解答的,“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对象性的方式改变对象性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对象性现实和其他人的对象性现实的时候”,现存世界“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42),相反,“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4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以其鲜明的实践性表明了自己同费尔巴哈的“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我”以及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
三、“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
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44)。他们没有一个人想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关系(45)。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的夸夸其谈反映的是德国现实的悲哀,因为德国哲学只不过是法国现实在德国的抽象的空洞的词句上的反映,因而问题不再是“变革哲学”,而是“变革现实”。作为“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的《形态》一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46),“词句失去作用的地方,才是生活开始的地方,才是存在的秘密揭开的地方”(47)。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离开哲学的基地”、“把哲学搁在一旁”、“跳出哲学的圈子”、“离开思辨的基地”、“跳出意识形态”、从“影子”回到“原主”,从作为范本、理想的人回到现实的人。费尔巴哈所设定的“人”并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游荡在空中的幽灵,施蒂纳的“我”不是现实的我,而是“唯实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范畴的精神产物,只是形式逻辑中“不具真实姓名的某甲的我”,“这个‘我’、历史虚构的终结,不是‘肉体的’、男女结合而生的、不需要任何虚构而存在的我”(48)。相反,唯物史观的前提正是现实的、肉体的、男女结合——不是通过“批判”的行为(49)——而生的、不需要任何虚构而存在的、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观察到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个人。这些现实的个人投身于其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再是“解释世界”,不再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新观念反对一种旧观念的斗争,而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50)。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不是“理想”,首先就是为了划清共产主义和一切意识形态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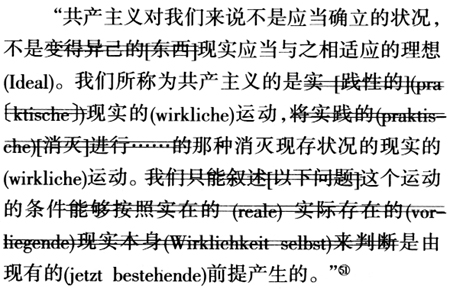
理想(Ideal)、理念(Idee)、意识形态(Ideologie)、唯心主义(Idealismus)的一致性甚至可以从词源上看出(52),对于马克思而言,它们都是哲学、词句、抽象、范畴,都是“解释世界”;与此相区别,在描述“共产主义”的时候,马克思连续使用了实践的——即“同理论有所区别的实践”(53)、现实的、实在的、实际存在的、现有的等用语。也就是说,与意识形态家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公然声明了共产主义的世俗性——“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54)。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实的“改变世界”的最实际的运动,而“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5)。
作为世俗的、经济性的运动,共产主义已经不再关注观念领域中“实体”和“自我意识”纷繁复杂的斗争,而是深入到这些观念所由产生的现实基础中,去解决现实自然和现实的人的矛盾。“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56)。因此,“人和自然的统一”就不再是一个“命题”,不再通过“实体”消融于“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被“实体”压倒的办法来解决,而是要实现现实的人和现实自然的和解。
起初,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是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自然界作为“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57)与人相对立,这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即是“对象意识”——人对自然界采取的是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所要达到的,是将人和自然界的物的关系、对象的关系提升为人的关系、自我关系。自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是人自身的对象化和对象化了的人自身。也就是说,自然就是人的无机身体,人就是自然的有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的自我关系。随之,现实中人的自我关系在头脑中即被反映为“自我意识”——人既把自己看成自然,同时在自然中看到自己。因此,这种共产主义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8),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9),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0)。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实的共产主义作为“人和自然界的现实的和解”,同时也“知道”这种解答,也就是说,随着现存对立的解决,思维和存在、自我意识和实体、个体和类等等这些“解释世界”的问题,也就被“知道”了。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61)——现实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也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的生成运动”(62),是第一种运动主导、统摄下的双重运动。这也就解释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共产主义不但是运动,而且是区别于思想运动的现实运动,伴随着现实的运动,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根基。
至此,我们说明了“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第一层意思——它是现实运动。事实上,这一点已经导向了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哲学范畴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和意识形态家的思维方式的深层区别——生成论还是预成论。
所有的意识形态家在以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按照自己关于神、标准人等等的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因此,全部历史不外是标准人以现实的个人为工具实现自身的过程,在这些个人中“人”或者“我”得到了发展,或者说这些个人发展了“人”或者“我”——当然,所谓的发展不过是意识领域中自我发现、自我启示而已。隐藏着的意思是,标准人作为具有创造力的范畴早已经以潜在的、隐蔽的形式存在着了,所有要做的仅仅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发现”将标准人的理想找出来,展示出它的内容、实现它。于是,历史上的所有事情都已经由先知——根据先验的目的——安排妥当了,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实现最高理想的一环,在历史进程中,后来的历史(63)则是先前历史的目的,例如,“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法国革命的爆发”。这样一来,历史的最新成果就变成了标准人“实际上历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实现,就好比“基督教在实际上一开始就除了给自己提出实现‘人’、‘真正的人’的任务外,别无其他”(64)。按照这样的理解,苏格兰地产制度“历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羊吃人,资产者“历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下笼罩在家庭上含情脉脉的面纱、实现家庭的非真理性,“大批患瘰疬病、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历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直截了当地驳斥了这种呓语——“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65),恰恰相反,“人们丝毫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的意图,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使社会发展起来”(66)。
马克思关于“主体在历史中生成”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奠定其哲学思想基本框架的《博士论文》中,在那里,偏斜——原子论科学中作为否定的第二环节——在“时间”中说明了历史性生成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直线下落运动的缺陷在于,它是一种由外力、重力决定的必然性,其中,原子的独立性、个别性、个体性、坚实性、空间强度、绝对性被扬弃了。因此,如果仅仅把原子视为沿着直线下落的东西,那么,原子的个别性规定还根本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原子根本就没有完成。这是因为,真正的原子——即使仅仅从空间上来看——也是“抽象空间的直接否定”(67),而“即使从空间的角度来看”(68),真正属于原子的运动也不是直线运动,而是脱离直线的偏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使用了“即使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字眼,它说明,脱离直线而偏斜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与空间的外在性相对立、维持自己于自身之中的坚实性即强度,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原则才能达到,这种原则就它的整个范围来说是否定空间的,而这种原则在现实自然界中就是时间”(69)。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原子的独立性、个体性、自由等等的生成只能借助于唯一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不是“从空间角度看”的“脱离直线而偏斜”,恰恰相反,这条原则“就它的整个范围来说是否定空间的”,它“就是时间”!原子的独立性只有在时间中才能够生成!
这里所谓的“时间”,不是物理学中的时间,不是牛顿时间、德谟克利特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是实体化了的时间和时间的实体化,就是实体,因而是成为绝对时间的时间,实际上不再具有时间性了。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就像金子被碎成许多小块一样”(70)是超时空、非时间性、非历史性、非生成性的,原子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排列组合中的、外形上的、外在的、非自身性的差别,比如A不同于N,N不同于Z。相反,对于伊壁鸠鲁(马克思)来说,真正的差别是时间性的差别,是主体在时间中生成性的、“历史的差别”。时间不再是物理学中的时间,而是哲学中的时间,当它被从本质世界中排除出去后,就成为了现象世界的主动形式、绝对形式、纯粹形式,它在现象世界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概念在本质世界中的地位。时间不是偶性,而是偶性的偶性,不是变换,而是变换的变换、自身反映的变化。也就是说,正是在时间中,现象才生成为我们看到的现象,犬才生成为我们看到的犬的样子、生成为“家犬”或者“猎犬”,人才生成为现时的人、生成为“搬运夫”或者“哲学家”。现象世界的一切都在时间中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生成,而时间就是否定性、扬弃性、发展性、历史性、生成性本身。因此,人是时间中的生成性的存在,共产主义是时间中的生成性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学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71),共产主义运动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所臆造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唯一实际的驳斥。
综上所述,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范畴,而是现实的个人对现存世界的变革运动;不是先验的存在于先知脑海中的完满典范或抽象理想的实现过程,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生成性的运动。
四、结论
至此,马克思为什么说“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谜底被彻底揭开了。首先,它的特定背景是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不论赞同与否——都把共产主义理想化了,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积极地赞同这种做法,而鲍威尔和施蒂纳则反对之。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不是理想”就是要划清自己同这对立两派之间的界限。其次,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是在现实发展缓慢而热衷思辨的“德国这样一个泥潭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因此,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不是理想”并不仅仅是要反对以上被点名的个别人物,而且是要反对在思辨中空转圈子而不朝外面看一看的、只能“解释世界”的“哲学”,表明要“跳出意识形态”、“离开哲学的圈子”,要“改变世界”。最后,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不是理想”是为了强调共产主义的实践性,而这种实践已经不再是哲学家口中的实践概念、实践范畴,而是“同理论有所区别的实践”,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是一种时间性的、历史性的、生成性的运动,同时,随着现存世界中对立的解决,对德国哲学家们来说的神秘力量——词句、观念、圣物——也将被真正地、实际地消灭。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②“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然后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其中〈〉内为马克思所加。见[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③这是广松涉的解读。见〔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④[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367页。
⑤[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1-672页。
⑦这是恩格斯对名为“青年英国”的团体的批判,后者的目的正是幻想“恢复昔日‘美好的英国’以及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3-494页。
⑧[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茶化”大概相当于汉语的“调侃”之意,即对严肃的内容进行“调侃”(见译者注①)。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11)首先,恩格斯所讲的是分工的问题;其次,在“田园诗式共产主义社会”的上一段,恩格斯的笔迹中明确提到了不仅仅是“观念”,而且首先是“现实”;第三,马克思对“田园诗式共产主义社会”的“茶化”在手稿第17页已经完成。
(12)“而且是理想化了的”(und zwaridealisiert)是马克思在手稿上新增加的。见[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3页。事实上,马克思看重的并不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而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关于这一点,唐正东教授在《青年马克思的现实人道主义概念为什么很重要?》(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16)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特意提到了马克思。他说:“为了把我完全与人等同起来,有人发明和提出了要求:我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类的存在’”。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2-19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页。
(22)参看[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
(25)对这种落后,恩格斯的说法是:“德国人是白痴式的;在英法是异族人移居于已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移居于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国,土著居民安居不动。”小林昌人认为,这是恩格斯的自虐性对比。见[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7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30)这方面的例证可以从马天俊教授《对〈共产党宣言〉中国化的一点反思——Gespenst如何说汉语?》(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一文中看到。马天俊教授认为:“马克思至少有一次庄重地把在他看来由全部人类历史运动为其准备条件的、并且作为全部人类历史运动的内在要求和趋向的共产主义隐喻为带有黑格尔哲学‘精神’的、半形而上学的‘幽灵’,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之语。”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页。
(36)马克思用“怪影般的影子”(eingespenstigeSchatten)和“伴随着的、独立了的影子的原主”(InhaberanliegendenemanzipiertenSchattens)比喻哲学范畴和它所由产生的现实基础。
(37)在德文中,positiv兼有“实证的”和“肯定的”意思。在《形态》序言中,马克思评价“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所强调的不是别的,正是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证唯心主义”被更明确地表述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页。
(45)马克思对于这两者的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仍然断言,德国现实还没有发展到德国哲学的高度,“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6页。译文有改动,原文为:Dies “Ich”, das EndeeinergeschichtlichenKonstruktion, istkein“leibhaftiges”, fleischlich von Mann und WeiberzeugtesIch, das keinerKonstruktionenbedarf, um zuexistieren.
(49)鲍威尔认为,“批判”是惟一的生产部门,人是靠批判的行为才被创造的——亚当批判了他的妻子夏娃,而她就怀孕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5-106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6页。
(5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11页,单双删除线的内容为马克思删去。
(52)据权威的“杜登词典”(
http://www.duden.de/),这些词都可以追溯到希腊文idea。Idee:”zumTeilunterEinfluss von franzA1Y702.jpgsisch idée <lateinisch idea <griechisch idea”; ideo-: ”zugriechisch idea”; ideal: ”zulateinisch idea”.
(53)马克思认为,过去一切哲学家所说的“实践”不过是“理论”的异在形式,它和理论的差别仅仅在于,后者是以理论面貌出现的理论,前者是以实践面貌出现的理论,也就是说,实践就是理论、理论就是实践,两者都是理论。“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的同一,在批判那里作为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重复着。因此,批判怒气冲冲地反对那种还想同理论有所区别的实践,同时也反对那种还想同把某一特定范畴变成‘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做法有所区别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6页。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63)这个“后来的历史”还有可能在事实上是先于“先前的历史”发生的。比如在黑格尔的哲学史中,巴门尼德就先于赫拉克利特登台亮相;在施蒂纳“人的唯一的历史”中,希腊哲学被安排得先于塞索斯特雷斯远征。
(64)[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2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译文有改动,“这种原则就它的整个范围来说是否定空间的”一句原译为“这种原则是否定空间的整个范围的”,不妥。原文为:das den Raum seiner ganzenSph? renachnegiert. ”此据贺麟先生译本改。参看贺麟译本《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网络编辑:嘉扉
 English
English